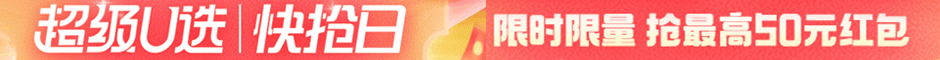光武帝为何退功臣而进文吏
南北功臣的制衡艺术
光武帝通过征伐建立千秋伟业,因此在建武元年(25年)六月即位时,他不仅未削减功臣的权力,反而赋予他们显赫的职位。据万斯同所著《东汉将相大臣年表》,当时除了太傅卓茂外,大司马吴汉、大司徒邓禹、大司空王梁等人均是开国功臣,他们在国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建武二年正月,光武帝依据“功次轻重”的原则进行分封,使得这些功臣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。据《光武帝纪》记载,光武帝将功臣封为列侯,大国享有四县的封地,其余各有差异。尽管博士丁恭引用古制进行规劝,但光武帝坚信,古国之所以灭亡,皆因无道之行,而非功臣土地过多。这种态度使得文吏在当时并未得到与功臣相当的待遇。《后汉书•侯霸传》中提到,侯霸因熟知旧事,逐步升至大司徒之职,但在建武十三年(37年)去世时,光武帝才下诏表示悼念,并提到因功臣尚未封赏,故未及时给予侯霸爵命。这进一步印证了文吏在当时的地位远低于功臣。
这些建武功臣不仅拥戴光武帝称帝,还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,有时甚至展现出压倒光武帝的趋势。例如,《后汉书•王梁传》记载,王梁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,擅自征发军队参战,虽然后来被光武帝赦免,但也显示出功臣在当时的权势。
虽然并非所有功臣都如王梁般恣意妄为,但相较于文吏,他们确实更难控制。范晔在评价光武帝“退功臣进文吏”的政策时,强调了光武帝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。然而,更深层次的背景是,光武帝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,需要对功臣进行有效的制约,而文吏则成为他施政的得力助手。鉴于功臣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,光武帝不得不采取策略,使南北功臣相互制衡,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。
在光武帝转战河北时期,他的手下功臣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派。南人指的是那些从南阳、颍川追随光武帝进入河北的早期僚佐,如邓禹等人。这些人地域观念强烈,常常怀念故乡。而北人则可能是指那些后来加入或在河北地区招募的功臣。这种南北之分,为光武帝提供了一个平衡各方势力的机会,使得他在维护皇权的同时,也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与繁荣。
"北人"通常指的是在光武帝抵达河北之前已在当地活跃,并随后加入光武幕府的人物。其中,大部分为河北土著,如王梁等六人在《后汉书》中有详细记载。尽管耿况、彭宠、景丹、吴汉等人的籍贯并非河北,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此地生活和工作,多数已在地方郡县担任要职,对河北的乡土情感逐渐淡化,并在政治上与当地人士形成了共鸣。
光武帝在河北地区通过消灭王郎、铜马等势力,奠定了建国的基础。在这一过程中,北人特别是来自上谷、渔阳等地的将领,因在平定河北的战役中表现出色并建立了显著的军功,因此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了显著地位。当时的最高官阶为三公和诸大将军,其中北人占据了五个席位,而南人仅有三个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大司马这一位居三公之首的重要职位,所推荐的人选均为北人。光武帝还特别提到了景丹作为“北州大将”的身份,他在上谷长史的职位上,因在援助光武的同郡僚佐中地位最高,而获得了“大将”的尊称。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在选官时,北州诸将普遍享有优先权的社会舆论。
随着北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势逐渐凌驾于南人之上,光武帝采取了一项基本策略:利用南人来制衡北人的势力。据《后汉书•邓禹传》记载,光武帝在遥授邓禹为大司徒时,并未提及他在河北的军功,这证明了邓氏在河北的战功并不显著。实际上,邓禹在河北平定后才被拜为前将军,其地位在北人如吴汉、耿诸大将军之下。光武帝即位仅五天后,邓禹在安邑击败了更始将王匡。仅过了七天,光武帝便以“平定山西”之功,迅速任命邓禹为大司徒。
邓禹上任后,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。尽管光武帝在北人占据军政要职的压力下做出了妥协,但仍有邓禹、朱祜、杜茂等南人跻身最高统治层。这明显体现了光武帝扶持南人以便尽快掌控新政权的意图。
南人凭借皇权与北人进行抗衡,而皇权则利用南人来遏制北人权力的扩张。这种政治格局构成了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。光武帝大力提携南人的行为,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也有所体现。例如,《后汉书•郭伋传》中提到,建武十一年(35年),郭伋调任并州牧时,曾到京师谢恩并受到光武帝的接见。在谈话中,郭伋提到选补官员时应该选拔天下的贤俊,而不应只局限于南阳人。这一观点得到了光武帝的认同,说明“选补众职”“专用南阳人”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郭伋在西汉末曾任渔阳都尉,王莽时期又拜为上谷大尹,与北州人士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光武帝在平定彭宠叛乱后,将郭伋转任渔阳太守,可能是想借助他在当地的声望来稳定局势。因此,郭伋对光武帝用人的批评也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北人的观点。
光武在此后的统治中确实做出了相应的调整。《后汉书•寇恂传》中记载,建武十二年(36年)寇恂临终前,时人赞誉他具有宰相的器质。然而,光武并未顺应众人的意愿,任命寇恂为相,而是让他在执金吾的职位上走完了人生。这一决定无疑揭示了光武与功臣之间地位的变化。再看《后汉书•贾复传》,建武十三年,贾复卸任左将军,以列侯的身份回归故里,并获得特进的荣誉。尽管朱祜等南人极力推荐贾复为宰相,但光武以整顿吏治为由,未采纳这一建议。贾复作为南人代表,而力荐他的朱祜也是南人。寇恂是北人,推举他的“时人”是否为北人已无从考证,但南北两大功臣集团都在为自身利益而努力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,光武的策略是将北人寇恂和南人贾复都排除在三公之外,这既体现了南北功臣之间的权力制衡,也为新兴政治势力和君主专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。
光武在建武中后期逐步解除功臣的兵权,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又一重要举措。这一行动始于建武十三年四月,当时光武帝废除了左右将军的职位,建威大将军耿也未能幸免。左右将军分别由贾复和邓禹担任。废除将军职位的背后原因在于,贾复深知光武希望停止战事,发展文治,不愿功臣在京师掌握重兵。因此,他与高密侯邓禹一同放弃军权,致力于儒学。光武对此深表赞同,遂废除了左右将军。功臣在京师拥兵自重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,光武对此深感忧虑。因为功臣一旦拥有将军名号,便可领兵,因此光武解决这一隐患的关键在于剥夺功臣的军职。
当时,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、北州大功臣耿。然而,光武并未从他开始下手。南人贾复、邓禹揣摩到了光武的意图,率先放弃军权。光武对此表示赞同,遂免去了他们的左右将军职位。虽然无法断定光武与贾复、邓禹是否事先密谋,但贾、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其他功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耿在权衡形势后,不久便上交了大将军印绶,交出了兵权。这实际上是耿在形势所迫下做出的无奈选择。此事清楚地表明: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,而真正的受益者是光武本人。
新臣与旧臣的更迭
《后汉书•窦融传》记载,当陇、蜀两地平定之后,光武帝命令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前往东都奏事。窦融到达洛阳后,主动上缴了凉州牧、张掖属国都尉和安丰侯的印绶。虽然窦融被引见并赐予了诸侯的席位,受到了皇室的恩宠,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旧臣,因此在与功臣们同朝共事时,表现得异常谦卑恭敬。然而,这种谦卑并没有使光武帝对他产生疏远,反而更加亲近和厚待他。窦融虽然小心谨慎,但仍然感到不安,多次辞让爵位。
窦融在建武十二年进京,当时的东汉朝臣确实存在新旧之分。那么,“新臣”与“旧臣”是如何界定的呢?从窦融的经历来看,他虽然在河西地区有着显著的功绩,但由于长期与中原隔绝,并未参与光武帝在河北的经营以及后续的战争。因此,与邓禹、吴汉等早期投入光武事业的“旧臣”相比,窦融等人只能算是新加入的势力。
“新臣”与“旧臣”的划分并非基于是否取得军功,而是基于他们依附光武帝以及入朝的先后顺序。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定后才奉诏进京,他们的经历与“南人”、“北人”有着显著的不同。尽管他们在地方上长期奉行东汉的政令,接受光武帝的封拜,但在朝廷中一直未能占据一席之地。
光武帝对待窦融等新人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。从窦融获得诸侯位、受到恩宠到拜为冀州牧、再迁为大司空,他的地位逐渐上升,实权也在增加。这种变化不仅使窦融本人感到显赫,也反映了光武帝对新臣的重视。此外,新臣多与皇室结亲,即使在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,新臣仍被赋予军事重任。建武、永平时期,窦、梁等家族权势显赫,甚至有凌驾旧臣之势。
然而,新臣的崛起也引起了旧臣的反感。例如,《马援传》中记载的建武二十五年春,马援所率的汉军在壶头遭遇五溪族的狙击,士卒多因疫病而死。耿舒上书指责马援贻误战机,导致失利。此事被光武帝得知后,派梁松责问马援,最终马援因病身亡。
马援虽然一向将梁松视为晚辈,但他的不幸遭遇梁松的陷害,实际上是新臣间因门户之争和长幼有序而引发的冲突,与本题的核心议题并无直接关联。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,实际上两种路线各有利弊,光武帝也难以做出明确决断,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马援的用兵失误。
耿氏兄弟在旧臣中占据重要地位,耿更是北州的名将、建武元勋。尽管史籍中并未记载耿有任何过激的反应,但如果他确实怀有“重立大功”的雄心壮志,那么他不可能会容忍新臣如马援在军事上屡次受到重用,而他自己却长时间陷入“无复尺寸功”的困境而无动于衷。耿舒对马援等“新臣”所使用的“伏波类西域贾胡”的鄙夷语气,暴露出他对新臣的偏见。耿氏兄弟及可能存在的其他旧臣,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了一致的立场,他们实际上是在质疑光武帝的用人方针。
那么,光武帝为何要“舍旧臣而任新进”呢?这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、伸张皇权的目的。如前所述,作为“旧臣”骨干的南北功臣集团在建武前期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,不断对光武帝的专制地位构成冲击。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关系错综复杂,他们暗中勾结,彼此呼应,难以动摇。相比之下,“新臣”在东汉朝廷中势力孤单,缺乏支持,唯有依附皇权才能立足。光武帝极力拉拢新臣,并借以打压旧臣,这或许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明智选择。
《后汉书》中提到:“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,外戚与政,上浊明主,下危臣子,后族阴、郭之家不过九卿,亲属荣位不能及许、史、王氏之半耳。”按照《东观汉记》的观点,光武帝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,严格防范外戚干预政治。阴、郭两家固然是外戚,而窦、梁两家同样也属于外戚。窦融位至三公,“在功臣之右”;梁松“贵重朝廷,公卿以下莫不惮之”,这些都已经为史籍所记载。
“前代权臣太盛,外戚与政”导致了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,这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立国家的光武帝来说,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。然而,他最终还是赋予了外戚极大的权势,未能真正摆脱西汉的窠臼。《后汉书•阴识附弟兴传》记载,建武二十年(44年)夏,“帝风眩疾甚,后以兴领侍中(按兴本官为卫尉),受顾命于云台广室。会疾瘳,召见兴,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。”尽管这一提议最终因阴兴的坚决推辞而作罢,但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,实际上已经在光武帝的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。这表明所谓“后族阴、郭之家不过九卿”的结果,并非光武帝的本意,《东观汉记》的说法并不准确。
导致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光武帝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,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。因此,光武帝必须不断寻找新的臣子来牵制旧的臣子。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的特殊性,容易得到信任。如果他们同时也具备从政的能力,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光武帝优先考虑的对象。
回顾东汉一朝的历史演变,窦、梁、马等家族之所以能够逐渐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外戚势力,并对政局产生深远影响长达百年之久,其根本原因在于建武年间光武帝所采取的扶植新臣的策略。
文官与武官的进退之道
《后汉书•光武帝纪》中论及东汉初年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现象,将“功臣”与“文吏”并列,并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主要标准。然而,这里所说的“文吏”实际上涵盖了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,与单纯将“文吏”与儒生对立的含义有所不同。
回顾史籍,我们发现建武年间受到光武帝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备儒学背景,如卓茂、伏湛、侯霸、欧阳歙、蔡茂、杜林、桓荣等人,他们或是“通经名家”,或是“避世教授”,多为儒者所推崇。光武帝中兴之初,为了充实和运转东汉的国家机器,急需大量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的支持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,令人困惑的是,光武帝麾下并不乏此类人才的功臣,但他却偏偏选择不用,坚定地执行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策略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
事实上,建武时期的功臣们普遍存在着居功自傲的情绪。如果光武帝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,他们难免会对皇权产生离心倾向,彭宠之乱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彭宠作为北州功臣的代表,其叛乱源于与“年少骄躁”的朱浮的冲突,但朱浮的背后常常有光武帝的影子。光武帝支持朱浮加强对彭宠的监控,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兵戎相见。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。
在彭宠起兵后,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帝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,推测他将会亲征。然而,事实上光武帝仅派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,并在邓隆、朱浮两军败退后,放弃了渔阳,听任彭宠割据称雄。光武帝在处理此事时显得畏首畏尾,似乎有难言之隐。他可能是担心一旦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,会引发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。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的领袖人物,虽然吴汉、王梁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,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彭宠而敌视朱浮的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南北、新旧功臣间的界限逐渐模糊,出现了融合的趋势。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。贾武仲与马姜的婚姻无疑密切了两个功臣家族的关系。尽管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,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非孤例。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无疑增加了光武帝制御功臣的难度。
综上所述,无论功臣具备多高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,他们终究会被皇权所不容,最终需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。光武与功臣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,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,也存在制约和矛盾的一面。然而,历代史家往往过于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,这使得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演化的深入阐释变得困难。
光武帝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策略在其称帝之初就已初见端倪。当时,光武帝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,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。以大司徒一职为例,尽管光武帝更倾向于任命伏湛,但由于伏湛并非功臣出身,最终仍需由功臣邓禹挂名。然而,《伏湛本传》记载:“车驾每出征伐,(湛)常留镇守,总摄群司。”这表明伏湛以司直行的身份实际上掌握了极大的权力。至建武三年(27年),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,伏湛接任大司徒,这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。
从建武三年到三十一年(55年),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。除了韩歆因征战有功外,其余六人都是文吏出身。与此同时,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、最初也被功臣所占据的大司空一职,在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,也改由文吏宋弘担任。在同一时期的九卿中,文吏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,其中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伏黯等17人。
光武帝大量擢任文吏,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所带来的隐患,这彰显了他的高明之处。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,光荣地退出了政治舞台。杜笃所说的“功成即退,挹而损诸”,可以说是对功臣们共同归宿的贴切描述。